翻阅七堇年的社交媒体,就会发现,这位印象中安静创作青春文学的作家,如今的日常大多是攀岩、洞穴探险、滑翔伞……
很难想象,一位作家发布的视频,却常常会被平台挂上安全提醒:“笔记含有危险行为,请勿模仿。”

从16岁那年,凭借《被窝是青春的坟墓》入围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算起,七堇年已经写作了整整23年。她说,写作曾经能带来的那种“全身心溶解于当下”的心流感,如今也越来越少了。
更重要的是,她发现,相比于写作的主观性与模糊性,运动的成就感才是确定的:一场马拉松,完赛了就是完赛了;一座山峰,登顶了就是登顶了;岩壁上的一条线,拿下了就是拿下了:“这种确定的正反馈,以及运动过程中的心流感,如此迷人,让我欲罢不能。”
于是,那些关于户外的故事,被她写进了最新小说集《巧克力与佛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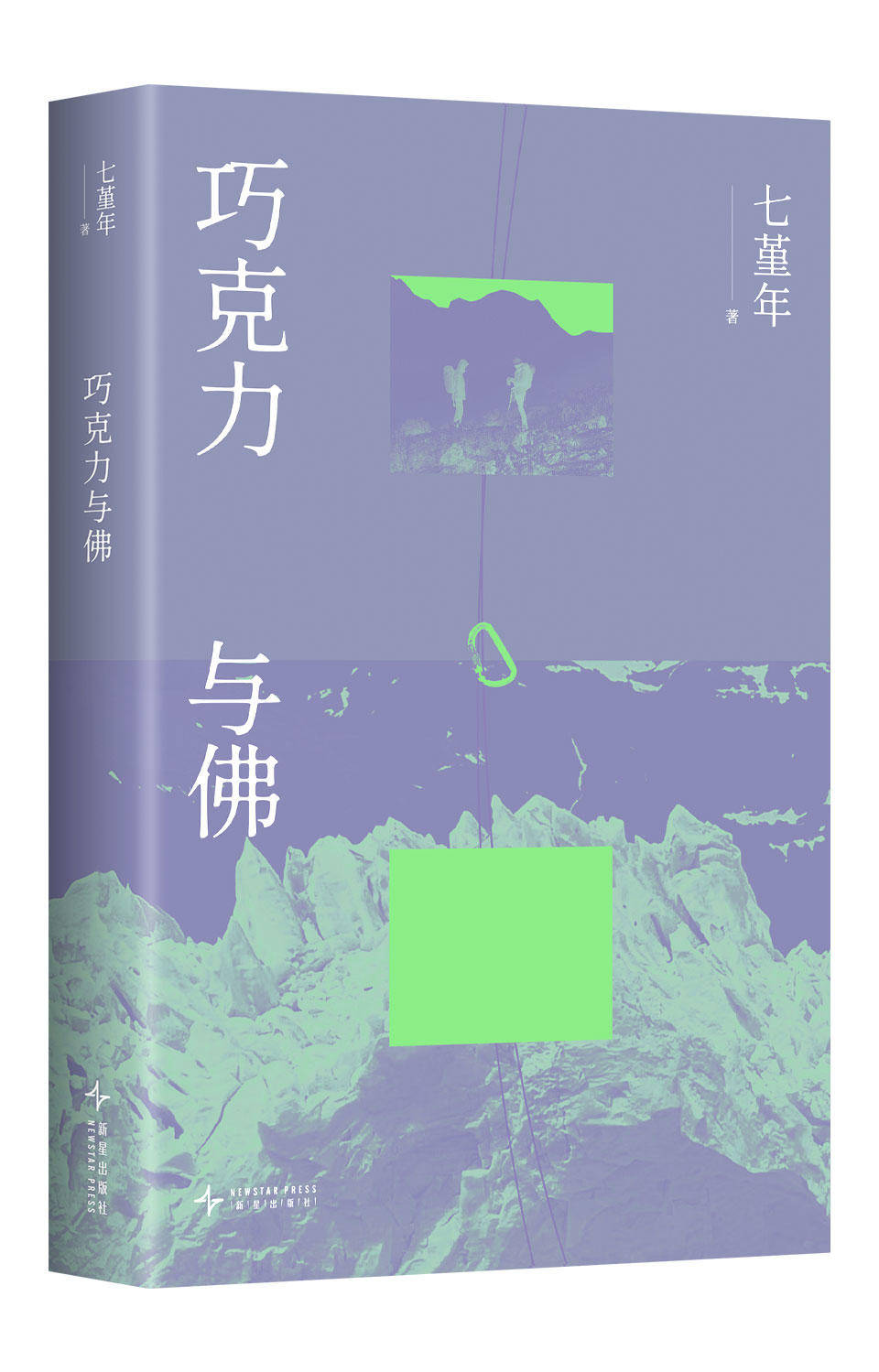
壹
“我的生活如今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从一个多愁善感的青少年,成为一个自爱、自在、自主的成年人。”回望早年的文字,七堇年在采访中说,那时候大多表达的是关于少年人的压抑和彷徨,但也不可否认那些是非常真切和不可避免的人生阶段。
“到现在仍然觉得被考试和作业‘荒废’掉的时光十分可惜。应试教育的副作用仍然残留在很多观念里——畸形的竞争急迫感,抢夺感,不配得感……这些都是一个小城做题家内心深处的烙印。”
真正的转变来自离开校园、步入社会。“变成一个成年人,有了时间与经济的独立,才谈得上自主,自由,才说得上“有了主体性”。”她开始开拓自己的兴趣,逐渐从徒步和旅行开始触摸户外探索,重新叩问内心: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热爱的?

图据七堇年
“写作太‘人’了,源于人,关于人,可如今的我想活得不那么像人一点,(而是像)动物一点。”她说,哪怕我们好不容易进化了几万年,终于造出汽车飞机火箭卫星,但最开心的时候仍然是变回猴子的时候——奔跑、跳跃、攀爬。“我把它形容为:返祖的快乐。”
那是一种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明白的感受。
就像在她的小说《巧克力与佛》中,男主角第一次登山时,就遇到神迹般摄人心魄的景色:……厚厚云层被捅了一刀似的,破了一个大口子,阳光如金色的血倾泻而出,流进雾中,凝成一段淡淡的虹。
但当他呼唤同伴快看时,流雾迅速淹没山巅:一切都羞涩地隐去了。

横断山脉一角 图据视觉中国
“攀登并不是为了风景。风景是一种偶然,是幸运的奖赏。”过去,七堇年习惯于结果导向的思维,而如今,登顶与否、美景是否出现,都不再是意义的全部。她说,那只是一种人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而所做出的“出格行为”。
山当然并不总是温柔的。第一次攀登海拔5000米的雪山,途中七堇年遭遇持续下雨,能见度不到五米,让她一度觉得自己“像在一团牛奶中行走”。

七堇年 图据出版方
“进入山野,无论是登山还是徒步,几乎每次出发,我们都面临着各种不确定和对自然的未知。”她说,最主要的体验就是肉体上的辛苦,高反带来的头疼、恶心、呕吐,让她觉得“身体和眼睛都在地狱”。
可正是在这种极端体验里,她开始思考:为什么安逸的生活并不构成最终解药?为什么躺在沙发上刷手机,喝快乐肥宅水,吃炸鸡的快乐,不能满足一个真正的人,至少不能“持续性”满足一个人?
相反,那些折磨人的时刻,反而让她更能确认自己的存在:“人通过这种折磨和刺激,能获得‘好吃懒做’所不能给予的深度——也就是那种,我活着,我在拼命呼吸——存在感。”

四姑娘山 图据视觉中国
贰
七堇年说,如今的生活,差不多已经达到了小时候理想的状态。看书,录播客,健身,着了迷一样地攀岩,花大量的时间进山。“对户外运动的热爱,母亲没有干涉过我,她当然也是担心的,但并没有阻挠过我。这也是她的改变,是我非常感激她的地方。”
她在城市中的生活变得很简单。早睡,早起,上午七点半便坐在电脑前,写作、处理事务、阅读。中午随意煮菜,饭后小憩,看书,然后去健身房或攀岩馆。晚上看看电影看看书,十点上床休息。
“我是城市中长大的孩子,很习惯城市生活。”虽然时常进山,但七堇年认为自己谈不上是“逃离城市”,“我甚至很感恩现代科技,让人能省出时间去做别的。”

图据七堇年
七堇年说,只是现在她不愿意困在城市中,不会把城市中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,当作全世界,“对于城市生活之外的世界,我同样保有极大的好奇和尊重,甚至是更重要的一部分。”
“写作二十年来,我已经从一个敏感而困顿的青少年,变成了那个‘以山为乐’的作家。”写作仍是她的精神静脉,但在写作之外,她的动脉全都流向了山地运动,滑翔伞、攀岩、攀冰、登山、洞穴探险,“它们是潘多拉魔盒,一旦打开,就再也没法合上。”
这些运动带给她的,更多是心灵上的治愈。
“攀岩是一种享受失败的运动”——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,七堇年震撼不已。那时,她还不会“享受失败”,成长的文化中也鲜有对失败的拥抱与肯定。那几年,她正身陷存在危机与虚无的泥潭,感到一切都失去了意义,活着也没有了乐趣。

四姑娘山双桥沟 图据视觉中国
她凭直觉走向自然寻求答案,进而深入了一系列户外运动,“从洞穴探险、滑翔伞到攀登……它们给了我存在意义上的出路和解脱。”
在某次攀岩的下午,七堇年突然顿悟:既然我可以如此毫无功利心地热爱一项运动,哪怕它毫无意义、百无一用,自己注定成不了高手,仍然乐此不疲,那我还有什么“无意义”不能接受?
辛辛苦苦登山,仅在顶峰停留一瞬就立刻下撤,什么也不图,就图个过程,甚至有可能根本上不去。她说,户外运动教会了她如何享受失败,在渺小的同时,还要倾尽全力而上。她说,自然带给她的是视野上的丰富,观念上的包容,“还有时刻提醒自己,人类很渺小,你很渺小,宇宙的本质是多样性,是无常。”

梅里雪山 图据视觉中国
“之所以说攀岩救了我,一方面是因为这项运动的魅力,它所包含的哲学意义——纯粹的西西弗斯式行为,上去,下来,一再如此,什么也不为,只为那个过程。”
那种身体与精神的切肤体验,让她真正化解了虚无的危机,也化解了“不走大路”的焦虑:“一个人可以通过如此简单和纯粹的方式获得存在价值感,满足和快乐。”
叁
新书的书名“巧克力与佛”,看上去有些怪异,说的其实是一种既矛盾又协调的两面体。
灵感源自杰克·凯鲁亚克的小说《达摩流浪者》。在那本书里,一群天真又迷惘的年轻人,借助徒步、流浪、禅修与佛学,摸索生活的真谛,反抗资本主义“工作—生产—消费”的闭环牢笼。
其中有一幕,主角在登山途中又饿又累,几乎支撑不住,他非常想吃一块巧克力。同行的朋友对他说:“这块巧克力,就是你的佛。”
“在人生的大部分时候,‘巧克力’与‘佛’,就像忠与孝、鱼与熊掌、红玫瑰与白玫瑰、月亮与六便士。”七堇年说,“千百年来,生活中让人揪心的,常常也是这些两面煎、两不舍,既要又要,而那样的“巧克力瞬间”,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顿悟时刻,是命运的禅。

七堇年在成都的新书分享会
对她而言,巧克力象征的是“想偷懒、想耍赖、贪图安逸的本我”;佛则代表“渴望实现的超我”。
她说,自己谈不上做出过很“艰难”的选择,因为一个选择如果很艰难,代表着两者都很难取舍,或者对自己真正追求什么东西还不够清晰。“就我自己而言,除了健康和自由,没有真正难以取舍的东西,所以回想生活经历中无论是对工作,事业,有违本心的时候,并不觉得做出选择很难。”
但实际上,在《巧克力与佛》中,这样的冲突与不理解,却处处存在。

横断山脉一角 图据视觉中国
比如经常登山的女生康羽,第一次带骨科医生徐开进山,因为徐开严重高反,二人不得不提前下山。在返程的高速上,二人沉默良久。之后徐开向康羽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却是:“你的社保怎么办?”
当康羽真正受伤,躺在徐开的手术台上时,徐开望着这个心中只有高山的女孩,心中却不可抑制地想着:如果这台手术不那么成功,那么她就永远只能乖乖待在城市里,好好过日子了。
七堇年说,这些冲突都在于攀登运动自带的属性。它危险,而且理应危险。从事它的人不该轻视这种危险。
“而我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素材,它天然带有很多戏剧冲突的属性——人与自然的冲突,人与人的冲突,人与自我的冲突,它本身就是一种很动态,冲突性会很强的情境。把它作为素材,我觉得很合适。”
“也许大多数作家的生活是静态的,写的是家庭、都市、代际……这些主题早已被写尽。”七堇年说,户外运动带给她额外的素材,让她跳出柴米油盐的世界,来点儿新鲜材料。

贡嘎群山 图据视觉中国
“一个人如果对城市生活的便利和安稳完全习惯,很容易一叶障目,很容易以为身边那点东西就是全宇宙。”她说,因为和大部分人一样,生活在城市中,大都经历类似的成长轨迹和时代背景,“我担心自己的阅历单薄,不足以在写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,所以我将目光投向山野,投向更广博的存在,以弥补自身的狭隘。”
在七堇年看来,人具有巨大的弹性,去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活。如今的她,可能更想追求一种更接近自然和更野生的快乐。在她一条洞穴探险的图片下,她写道:“要一直像只动物那样活着,爬着,飞着。”


 2345浏览器
2345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
火狐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
谷歌浏览器